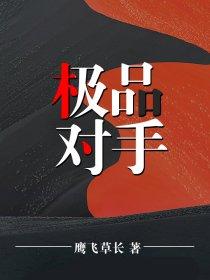芊芊小说网>我在唐朝做 > 第六十四章 整顿吏治首战风波(第1页)
第六十四章 整顿吏治首战风波(第1页)
寅时三刻,更鼓声隔着窗纸闷闷传来。案头烛火摇曳,一点烛泪滴落,在冰冷的青铜镇纸上迅速凝成半透明的琥珀色。
方羽将最后一页靺鞨文书压在砚台下,指尖似乎还残留着赤砂印泥特有的、略带刺鼻的气味。他抬手取下鎏金灯罩,昏黄的火苗立刻蹿高一截,无声地舔舐着桌上一封密信的边缘,将其化为灰烬。
“范阳三镇的粮仓账册,都核对清楚了?”他的声音在寂静的深夜里显得格外清晰。
商瑶端着一碗刚熬好的参汤,悄步走到紫檀木案几旁放下,裙裾拂过地面,带起几张散落的河图洛书图纸。
“幽州军仓账面登记存粮十二万石,我们的人实际清点,不足七万。”她从袖中抽出一方素白绢帕,轻轻擦拭方羽鬓角渗出的细密汗珠。“你让暗卫扮作粟特商人混进平卢军镇,查验军械库,倒是让杨国忠那个不成器的侄子,凭空多赚了三百贯的中介跑腿费。”
方羽伸手,握住她微凉的手腕,腕上缠绕的五色丝绳硌着他的掌纹,触感分明:“明日朝会,若还是压不住这群盘根错节的蠹虫……”
“那就让他们看看,什么叫雷霆手段。”商瑶抽出绾发的一支金簪,轻轻挑了挑灯芯,火光骤然一亮,映得她眉心那点嫣红花钿也随之跃动。“还记得天宝三载渭水决堤吗?你带着三百工匠,七日便筑起了二十里石堰。如今,不过是把垒堰的砂石换作人心罢了,道理是一样的。”
五更梆子声远远传来,厚重的朱雀门发出沉闷的吱呀声,缓缓向内洞开。
晨曦微露,清冷的空气带着露水湿气。方羽蟒袍前襟上绣着的螭纹,在初现的微光中仿佛流动起来,腰间蹀躞带上,扣着一枚崭新的银鱼符,那是昨夜商瑶亲手为他系上的。
杨国忠早已立在蟠龙柱巨大的阴影里,头顶的三梁进贤冠压着他已显花白的鬓角,面色晦暗不明。
“诸位同僚,可知如今长安米价几何?”方羽的声音不高,却足以让所有人都听清。他展开象牙笏板的动作带起一阵微风,惊飞了殿檐下几只宿鸟。“西市斗米十五文,寻常百姓皆知。但太仓出库的账簿上,赫然记着三十五文一斗——这凭空多出的二十文差价,足够养活半个京兆府无家可归的鳏寡孤独了。”
“铛!”杨国忠的笏板重重撞在身前的青铜龟钮上,发出一声闷响。“方国公倒是悲天悯人,却不知边镇将士浴血奋战,至今范阳驻军的冬衣还未曾发下!”
“冬衣?”方羽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,从宽大的袖中抖出一卷抄录的靺鞨文书,“据报,平卢节度使上月动用五万匹上等绢帛,向契丹部换取了十只海东青。这笔巨额开支,走的却是幽州军镇营房修缮款的账目。”他刻意停顿了一下,目光扫过几位面色有异的官员,“说来也巧,我们的人验看时发现,那批运往契丹的绢帛上,印着的官防,恰是剑南道的。”
朝堂上响起一片倒抽冷气的声音,不少官员下意识地看向杨国忠。
杨国忠攥着笏板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——剑南道转运使,正是他夫人的亲弟弟。
“方国公这是要效法来俊臣,罗织罪名,构陷朝臣吗?”他扯动嘴角,挤出一个僵硬的冷笑。
“那便说些无需罗织的。”方羽不为所动,轻轻击掌三声。殿外立刻响起沉重的脚步声,八名身着甲胄的金吾卫抬着四口包着厚铜边角的沉重木箱,鱼贯而入,重重顿在殿中。“自天宝五载至今,户部存档的鱼鳞册与各道州府上报的实际田亩数,前后相差竟达二十七万顷之巨。陇右道军屯按册应产粟米六十万石,实收却不足四十万石——这些被吞没的田亩和粮食,养肥了多少蛀虫?搜刮所得,怕是够在骊山脚下,再造一座金碧辉煌的华清宫了!”
杨国忠的喉结不自觉地上下滚动,眼角余光瞥见文官队列中的张九龄,正对着方羽的方向,几不可察地微微颔首。
那位老臣今日穿着的紫袍上,仙鹤补子似乎沾染了清晨的霜色,那是五更天在宫门外候朝时凝结的寒露。
“方国公可知,清查全国田亩,需动用多少胥吏?耗费多少钱粮?”杨国忠的声音像是生了锈的铁器摩擦,嘶哑难听,“这些刀笔吏一旦下乡,拿着鸡毛当令箭,怕不是要闹得地方上鸡犬不宁,民怨沸腾!”
“所以,本官今日请奏,重开匦院。”方羽说着,伸手解下腰间蹀躞带上悬挂的一个铜匣,托在掌心。匣子打开,露出一枚不过拇指大小,却铸造精良的青铜虎符。“凡有百姓检举官员贪墨情事,一经查实,检举之人可领涉案金额一成,作为赏金。”他故意将铜匣转动了一下,让靠近的几位大臣能看清匣底刻着的一个不易察觉的“商”字暗纹。
朝堂之上,忽然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。匦院,那是前朝则天皇后所设的检举机构,用以收集天下密报,安史之乱后便已废止,至今已有二十余载。重开匦院,其意不言自明。